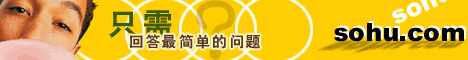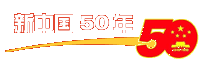
![]()
[返回]
您現在所在的位置: 國慶網站首頁>>最新報道>>報道內容
| 國慶大典評說:為了子孫后代,為了可持續發展 中新社北京十月一日電 國慶大典評說:為了子孫后代,為了可持續發展 中新社記者 尹丹丹 在今年的國慶游行中,當展現新中國環保事業面貌的方隊伴著因專題系列紀錄片《話說長江》而家喻戶曉的《長江之歌》進入人們視野的時候,中國人的心情也許會有點兒復雜:既感到自豪與充滿期望,又懷有深切的憂慮。 為什么會這樣? 因為,新中國的環保事業是“白手起家”,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一步步發展起來的:孕育于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開始被納入國家重要議事日程,在八十年代獲得了迅速發展,從九十年代起進入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八十年代初創辦的《中國環境報》還成了當時全球第一家國家級環保專業報紙;現在,全國約有三十多家地方環境報和幾百種環境專業期刊。 更為重要的是,在近些年經濟飛速增長、人口不斷增加的條件下,一些主要污染物的排放總量呈下降或持平趨勢,污染物處理率和達標率均保持著增長勢頭,全國環境質量總體保持穩定,部分城市和地區還有所改善,基本避免了環境質量急劇惡化的局面。這些值得自豪與贊揚。 毋庸諱言,與此同時也存在著令人憂慮的問題。按官方的說法就是:環境形勢依舊嚴峻,相當多的地區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的狀況依舊如故,甚至有的還在加劇;“三廢” (廢氣、廢水、廢渣)等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仍在增加,以城市為中心的環境污染在繼續,并正向農村蔓延。就拿長江來說,去年那場造成慘重損失的洪水的根源之一,就是人為的生態環境破壞。 不過,另一方面,民眾環保意識的普遍增強,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了環保與可持續發展間的緊密關系,保護環境和可持續發展均被上升為基本國策,以及國家從政策到資金上對環保事業的支持等,又是令人感到欣慰、能增強信心的積極因素。 眾多且還在增加的人口,相對匱乏的自然資源,仍顯薄弱的經濟基礎與技術能力,都已是國內外公認的現實。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正處于工業化與城市化發展極為迅猛的時期,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強度因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張而日益加大,隨之而來的是自然資源超負荷過度消耗,污染物排放量卻急劇增加。 同世界其他許多地方的情況一樣,中國人終于提出了可持續發展問題,并將環境的保護與治理視為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關鍵內容之一。 一九九六年,中國在《國民經濟發展“九五”計劃和二O一O年遠景目標綱要》中明確提出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將其作為中國在下個世紀的重要指導方針之一。兩年前制定的《中國二十一世紀議程--中國二十一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便成了實行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行動綱領。 在同年召開的第四次全國環保會議上,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指出“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最早源于環境保護”,而“保護環境的實質是保護生產力”。他把環境保護稱為“一項崇高的事業,是積德的事業,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環保被正式確定為一項基本國策,是在十六年前召開的第二次全國環保會議上。這次會議提出了對經濟、城鄉和環境的建設同步規劃、實施、發展,實現經濟、社會與環境三種效益相統一的戰略方針。 經過努力工作,到去年,全國工業廢水處理率超過了百分之八十七,工業廢水排放達標率為百分之六十五,工業廢氣消煙除塵率達到了百分之八十八以上;直轄市、省會城市以及一批大中城市,實現了車用汽油無鉛化,建立了環境質量周報和日報制度;城市居民用氣普及率為百分之七十三,供水普及率是百分之九十五;全國森林覆蓋率達到百分之十四,城市建成區的綠化覆蓋率達到了百分之二十四;建立了九百二十六處各類自然保護區,其中長白山、西雙版納等十處自然保護區加入了“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網”。 中國還積極參與全球范圍內環境發展領域的各項活動,簽署和加入了《保護臭氧層的維也納公約》、《關于消耗臭氧層物質的蒙特利爾議定書》和《生物多樣性公約》等十八項國際環境公約,并與二十四個國家簽署了雙邊環境合作協議,引進外資、先進科技和現代化管理方法。 這兩年,中共中央在“兩會”召開期間都安排了環保問題座談會,決策層領導直接聽取了環保工作匯報。去年的國務院機構大改革,將原來副部級的國家環保局提升為國家環保總局,并強化了其環境監督執法職能。 在投資方面,八十年代初中國每年用于環保的投資約占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零點五三;到八十年代末,這一比例提高了零點一個百分點;九十年代中期,比重升為百分之零點七三;去年,環保投入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已超過了百分之一。 而對環保事業發展具有根本性意義的措施還在于教育。目前,環保已納入九年義務教育,全國有一百四十所高校、上百所中專及職業高中開設了環保專業,共擁有環境類專業五十一個,碩士和博士學位的授予單位分別有二百二十三個和七十七個,此外還有若干博士后流動站。 中國人有句老話:前人栽樹,后人乘涼。走過一段彎路、犯過許多錯誤后,今天的人再次強烈產生了這種意識。不過,建設“一個美好的家園”傳之子孫后代,還需要中國人付出巨大的努力和艱辛的汗水。(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