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薄”之間的漢語哲學
【學術爭鳴】
光明日報近期圍繞“漢語哲學”組織的學術爭鳴,匯聚了這個領域代表性學者們的最新思考,也讓筆者有機會深化對漢語哲學的觀察和解讀。在筆者看來,一方面,漢語哲學的倡導者們呼應時代和社會需要,試圖賦予漢語哲學研究范式以“中國哲學”“漢語言哲學”等囿于傳統學科領域的研究路向所不具備的內涵和功能,從而豐富了當下中國的學術論說;另一方面,漢語哲學的倡導者們陷入了徘徊于加法與減法之間,厚概念和薄概念之間,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間的進退失據狀態。筆者認為,只有更深入地澄清基本概念、進一步完善論證手段,才能使這一路向的探究產生真正有意義的思想躍遷和學術增量。
在加法和減法之間
漢語哲學的倡導者之一韓水法在2016年發表的《漢語哲學的使命——特征、境況與前景》中枚舉了漢語哲學的“多重意義”,分別是用漢語作為思維和表達工具的哲學活動、一般所謂的中國哲學、漢語語言哲學和哲學的漢語翻譯,雖然這種“分類”本身并不周延,但這顯然是在試圖做加法,至于能夠加出個什么來則并不是顯而易見的,因為這四項相互之間包含重疊的內容,如果一味做加法,那些重疊的部分就有被計算多次之虞。與此同時,此文也試圖做減法,但是問題在于,減去那些“冗余”的,漢語哲學的內核還剩下什么呢?從文章的描述來看,漢語哲學最重要的規定性有兩個:一是強調用哲學回應人類的普遍性問題,這是為了凸顯哲學的普遍性維度;二是強調哲學與科學的合作,強調突破既有的學科藩籬。如果說前者所表征的是德國觀念論的理性主義傳統的影響,那么后者則體現了與作為20世紀哲學精神之表征的分析哲學的親和性,這在當下的中國哲學界——包括漢語哲學界——都是尤為難得和寶貴的。
在某種程度上,既體現了漢語哲學的加法精神,又體現了其減法精神的是韓水法的《漢語哲學:方法論的意義》一文,不過這里仍然有兩個可諍之點,一是所謂漢語哲學的方法論視角與以漢語為視域之間的含混與糾結,這是此文中方法論的宣稱與其“實踐”之間的某種“落差”給我們造成的印象;二是在這種方法論視角中所特別強調的漢語哲學主要是一種理論哲學而與實踐哲學甚少關涉的斷言,無論我們從當代哲學“實踐轉向”的視角,還是從漢語哲學可能的指涉來看,這種斷言至少是更為表面化的,或者是過于嚴苛的,其實質乃是做減法過甚的產物。
孫向晨的《“漢語哲學”論綱:本源思想、論域與方法》一文從普遍性關切、本源性思想和規范性建構三個方面提供了對漢語哲學研究的一個具有典型文本特征的描述和刻畫。此文中最為重要的是他對于本源性思想的強調,這個核心概念幾乎支撐了他對于中西哲學的所有重要的論述。孫向晨反復強調要超越比較哲學的思路和視野,但是頗為吊詭的是,他越是加強本源性思想在他的整體論述中的權重,就越會削弱他走出比較哲學舊轍的努力。當然,孫向晨運用了兩種重要的方法論資源,一是法國學者列維納斯關于“他者”與“自我”的“辨異法”,二是法國學者于連在中西哲學與思想之間的迂回策略。由此可以看出他既想做加法又想做減法的企圖心,這種企圖的最后結果就是他的雙重視野論或雙重本體論。
孫向晨明確反對所謂語言決定論,但是從他對中西哲學的刻畫和描摹來看,語言決定論對他的影響不可小覷。就此而言,韓水法那種似乎“圓熟”程度稍遜的普遍主義取向反而是某種有益的制衡力量,因為這種普遍主義更為徹底地擺脫了語言決定論的制約。在這里,我們應該援引梅祖麟早年從漢語缺乏屈折語的角度對斯特勞森之主謂語區分作出的批評。關鍵在于,基于英語的語法特征區分主謂語是一回事,這種區分本身在人類思維結構中的普遍性則是另一回事。這當然是符合斯特勞森本人的看法,他在晚年尚且重申,在此類問題上,文化相對性的論點是重要的,但其重要性可能沒有想象的那么大,“不管不同社會在背景差異方面是何等巨大,但是擁有這些差異的個別語言使用者都是相同的人類的成員”。同時,如果說在軸心時期,所謂本源性思想差異是一種構成性的差異,那么在后軸心時期的思想努力中,包括孫向晨等海內外學者們喜歡談論的“迂回”,則更多應該致力于將之轉換為一種背景性的或者二階的視域——事實上所謂迂回的策略要能夠奏效,也一定是以這種區分為前提的。
于是,我們可以在上述加減法中發現某種拉鋸,一方面是科學,另一方面是所謂本源性思想;一方面是方法論意義,另一方面是規范性指向;一方面是理論哲學,另一方面是實踐哲學;一方面是比較,另一方面是迂回,正是這種困局召喚著某種更深層次的發問和探索。
在厚概念和薄概念之間
也許正是基于這些已經指出過的困難,孫向晨在光明日報發表的《漢語哲學的基本問題向度》一文中,明確把漢語哲學界定為“基于‘漢語世界’的生存論經驗所進行的哲學探索”,從孫向晨賦予這種哲學探索的任務來看,如此界定首先是為了與其內涵為中國哲學史的“中國哲學”這個表述區分開來,因為后者被認為主要是面向過去的,而漢語哲學則由于面向哲學問題本身就不但是現時態的而且是指向未來的;其次是為了與從張東蓀到劉梁劍的漢語言哲學區分開來,因為漢語哲學所注重的并不是語言哲學,而是“漢語”所帶出的生活世界;最后是為了與用漢語書寫的哲學區分開來,因為漢語哲學的重心不在所使用的語言,而在“哲學”,而這種哲學的基礎就是漢語世界的生成論經驗。
龐學銓在光明日報發表的《“漢語哲學”三問》一文,在接受韓水法對于廣義漢語哲學和狹義漢語哲學之區分的基礎上,以嚴密的邏輯和犀利的論辯揭示了這個表面合理的區分下面潛藏著的更深層次的問題。在龐學銓看來,聚焦于漢語世界的生存論經驗和本源性思想會排除掉我們在日常的意義上已經接受為漢語哲學論域的內容和題材,例如那些似乎與漢語世界的生存論經驗和本源性思想距離比較遙遠的主題。龐學銓從方法論價值來為廣義漢語哲學辯護,堅持以漢語為載具是漢語哲學的標識性特征,認為廣義漢語哲學“既凸顯了漢語思考與哲學表達的關系,又表明廣義的漢語哲學本來就包含、容納了狹義漢語哲學”。
從表面上看,龐學銓和孫向晨的分歧僅僅在于是否要把諸如于連和安樂哲這樣不以漢語為載具的哲學研究包含在漢語哲學之中,但是其實質仍然在于對漢語哲學本質規定性的分歧。在這里,我們可以借用英國學者威廉斯的厚概念和薄概念來分析漢語哲學爭論中目前這個層面的分歧。之所以說是借用,是因為威廉斯是在倫理學中使用這種概念區分的,他把具有特殊內容的倫理概念,例如背叛和許諾,殘暴和勇敢,稱作厚概念,而把更為抽象和脫離共同體語境的諸如正義、公平這樣的概念稱作薄概念。與薄概念相比較,厚概念所表達的似乎是事實與價值的結合,“怎么使用這些概念,一方面由世界是什么樣子來確定,而同時,這卻通常也包含對處境、人物、行為的某種評價”。
由此來透視韓水法在光明日報發表的《漢語哲學的基礎、困難和前景》一文中對漢語哲學已經是一個“事實”的強調,會得到一些有趣的看法。首先,從歷史還是從現實來審視漢語哲學,會有一個視角上的差異,因為漢語哲學之問本就是新一輪的古今中西之爭背景下才產生的問題;其次,從文中的論證來看,存在著若干混淆,例如將“漢語哲學”與“人類生命結構及其遺傳特征”進行類比,進而指出“漢語哲學應當被視為對一種事實和現象的命名,而并非一個學科或方向”,這可以看作是前述做“減法”的某種殘留;最后,筆者贊同韓水法關于漢語哲學討論重心轉移的觀點,也樂見促進漢語共同體精神活動之動力涌現,但正因為如此,筆者才認為應該把漢語哲學理解為“事實與價值的結合”。
無論如何,厚概念和薄概念的區分還是值得借用的,借用這種區分,與哲學相較,漢語哲學就是厚概念;與廣義漢語哲學相較,狹義漢語哲學就是厚概念。之所以要使用“漢語哲學”這樣的“厚概念”,就是因為“哲學”表征著這個“世界”,而對“漢語哲學”的使用當然也表明了“對處境、人物、行為的某種評價”。在廣義漢語哲學和狹義漢語哲學這個對子中,賦予后者以“厚概念”身份的就是漢語世界的生存論經驗和本源性思想。本著這樣的立場,一方面堅持要把不以漢語為載具但被認為闡發甚至構建了這種生存論經驗和本源性思想的哲學運思及其研究成果納入漢語哲學中來,另一方面又認為漢語哲學要使用一種去語境化的理論方式表達自身對普遍性哲學問題的關注,這既可以說是像傅永軍敏銳覺察到的那樣包含了具有某種反噬作用的“矛盾”,也可以說是像龐學銓那樣平實地理解為“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關鍵在于我們在這里所面對的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矛盾和一個什么樣的問題。在筆者看來,矛盾之處和問題癥結在于當論者要強調的是漢語哲學的普遍性維度時,所使用的是薄概念,或這個概念的“薄”的一面;而當強調的是漢語哲學的特殊性維度時,所使用的是厚概念,或這個概念的“厚”的一面。在這樣的“宏大”問題意識支配下,有些“概念”和“技術”上的“細節”反而容易被忽略或者至少是變得主觀隨意了,而在哲學問題上,也經常是細節決定成敗,這應該是目前這場爭鳴雖有進展但是進展并不完全令人滿意的一個根本原因。
在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間
漢語哲學之問出于普遍性與特殊性之爭、漢語哲學之問向著普遍性與特殊性之爭、漢語哲學之問介于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這是當我們從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問題去觀察漢語哲學之問和之爭時可以得到的三個命題和結論。
說漢語哲學之問出于普遍性與特殊性之爭,是因為如果沒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問題的刺激及其內在的緊張,漢語哲學要么就成了純粹的發思古之幽情,要么就成了文化特殊主義的最新版本。說歷史上曾經“存在”漢語哲學和現實中已經“存在”漢語哲學,這兩種漢語哲學的含義是不同的,這兩種“存在”的含義也是不同的。前一種“存在”可以是一種“事實陳述”,但是其中的漢語哲學卻是一個厚概念;后一種“存在”是“事實與價值的結合”,但是其中的漢語哲學卻無法宣稱自己是一個“厚概念”,最多是厚薄之間的一個概念,這是厚薄之辯中一個悖謬之點,原因就在于漢語哲學之問出于普遍性與特殊性之爭。
說漢語哲學之問向著普遍性與特殊性之爭,是因為漢語哲學的提出就是為了措置普遍性與特殊性之爭。說漢語哲學之問出于普遍性與特殊性之爭,這是在“原因”層面講的;說漢語哲學之問向著普遍性與特殊性之爭,這是在“目的”層面講的。用威廉斯的話來說,“思考過去與思考未來所帶來的問題也不同,因為過去是我們的原因,而我們是未來的原因”。如果我們認同這一點,就會對漢語哲學之問向著普遍性與特殊性之爭有更為同情的理解,畢竟過去(歷時的“過去”應該也在不同程度上涵蓋共時的“外部”)是我們的原因;如果我們認同“我們是未來的原因”,就應該對漢語哲學之問如何向著普遍性與特殊性之爭有更為審慎和均衡的考慮,這也是為什么一個本身是“事實與價值的結合”的厚概念的漢語哲學,充其量只能是一個厚薄之間的概念,而無法像在歷史上曾經存在的那樣就是一個厚概念的主要原因。
說漢語哲學之問介于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除了基于上述厚薄之間的論辯,也是因為漢語哲學本身曾經貢獻過對這里的“之間”的某種獨特的理解。例如,張祥龍先生就曾經在一次討論會上提出“我們需要同時追求兩個極端,形成一個張力然后感受中間的東西”,他還問“能不能有這樣一個哲學?它直接闡發的就是中間的這一塊,而不是通過認為這兩者中某一個是更真實的然后來做”。筆者認為,在某種程度上,這就是于連所做的工作。
在《從存有到生活:歐洲思想與中國思想的間距》這部著述中,于連勘察了“之間”和“之外”之間的“間距”。在他看來,希臘人的本體論的邏輯思辨只思考極端的相反項,因為追求可當成定義的本質性,希臘人忽略了“兩者之間”難以指定的“過渡”,于連得出結論:“希臘人由于不懂思考‘之間’,就不得不思考‘形而上’的‘之外’”,而“道”這個“之間”無法讓人從任何一邊來界定,于是有庖丁入“有間”而游刃有余,“‘之間’是某種永不枯竭之源,也許是唯一的源頭,而不企圖‘推延’到‘之外’”,相反,“在‘之間’里,‘之外’是從‘之內’發現的”。也許于連作為一個“狹義漢語哲學家”在“廣義漢語哲學”更不用說“廣義哲學”領域并未得到足夠充分的——“之外”的——承認,但是他這番關于“之間”“之外”和“之內”的辨析無疑值得“之外”“之內”者深長思之,因為它是由一個“之間”者發出的。
在2022年召開的北京大學漢語哲學中心成立大會上,有學者將漢語哲學刻畫為從漢語里長出來的哲學。按照這種洞見,漢語與哲學的關系就像孔夫子與中國的關系,正如漢語哲學是從漢語中長出來的,孔夫子是從中國長出來的。啟功先生關于書法有一個金句:一幅書法作品可能是雄強的,但是我們不可能“雄強地”寫出一幅雄強的書法作品來。也許,我們最好不要將漢語哲學看作一個明確的學科甚至論域,而是看作一個吁求和一種呼聲,并在具體哲學研究實踐中予以推進。
(作者:應奇,系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學系教授)

文娛新聞精選:
- 2025年08月27日 09:51:35
- 2025年08月26日 14:17:45
- 2025年08月26日 10:04:51
- 2025年08月26日 10:04:01
- 2025年08月26日 10:02:35
- 2025年08月25日 19:24:33
- 2025年08月25日 18:49:45
- 2025年08月25日 18:35:56
- 2025年08月25日 15:10:03
- 2025年08月25日 14:48: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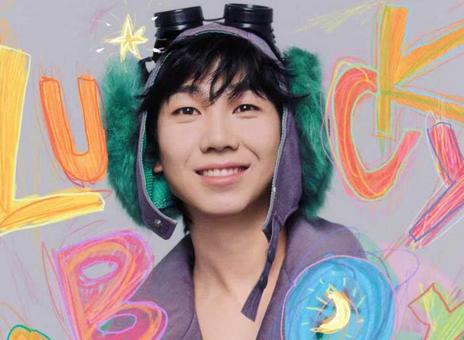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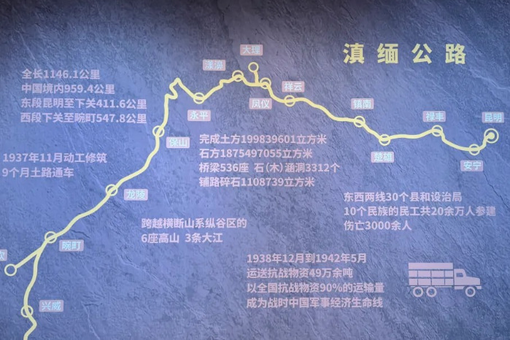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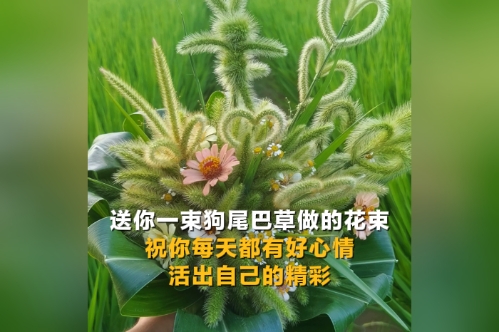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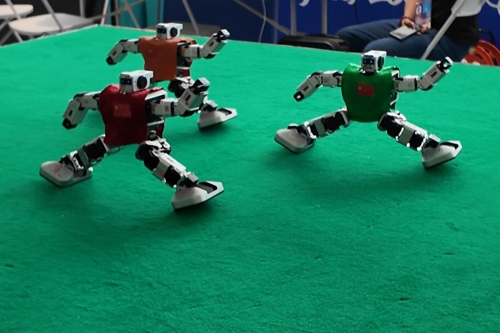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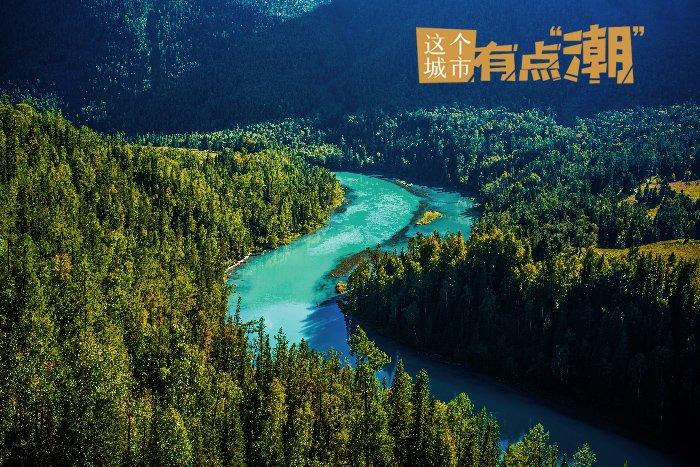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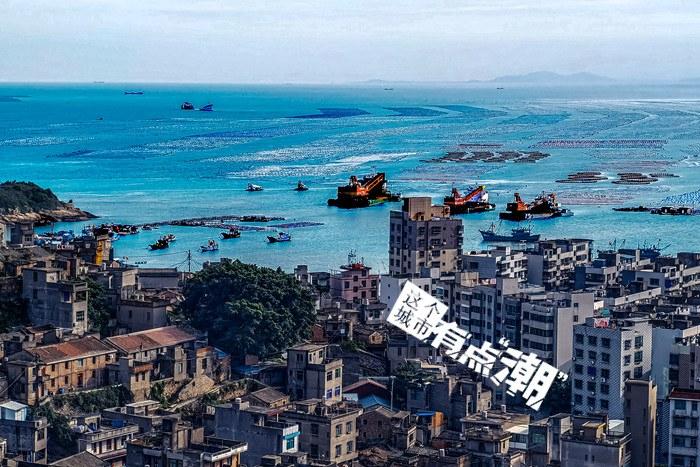


 京公網安備 11010202009201號
京公網安備 1101020200920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