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丨王祎:為何中文被86個國家納入國民教育體系?
中新社北京11月12日電 題:為何中文被86個國家納入國民教育體系?
——專訪溫州大學華僑學院副院長王祎
中新社記者 門睿

截至2025年9月,已有86個國家把中文納入國民教育體系。為何越來越多國家將中文納入國民教育體系?這傳遞出什么信號?海外中文教育如何應對?溫州大學華僑學院副院長王祎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這些國家將中文納入國民教育體系的具體實施路徑有哪些?
王祎:中文被眾多國家納入國民教育體系,代表性模式和路徑可歸納為以下三種。
從國家規劃層面納入整體教育體系的系統嵌入型。如俄羅斯不僅將中文納入國民教育體系,還自2019年起正式將中文納入國家統一考試的外語選考科目。南非在2015年將中文納入國民基礎教育體系,在2018年將中文作為第二附加語納入當地高等教育入學考試體系。
依托于緊密雙邊經貿關系和合作項目的雙邊合作驅動型。如泰國在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框架下,通過“中文+職業技能”模式將中文納入當地職業技術院校培養計劃,為合作項目儲備本土化人才。中阿合作的“百校項目”將中文課程納入阿聯酋公立中小學教學規劃大綱。一些非洲國家如埃及、突尼斯等也在小學到大學的各階段開設中文課程。
由社會需求自下而上驅動型,在經濟高度開放、市場嗅覺敏銳的國家尤為明顯。如愛爾蘭將中文列為“戰略外語”之一,主要緣于企業界對中文人才需求的強烈反饋。

中新社記者:這一現象展現什么特點?
王祎:縱觀全球,將中文納入國民教育體系的現象有三個鮮明特點。
地域分布多元化。中文教育已超越東亞、東南亞文化圈,呈現向中東歐、中東、拉美及非洲國家擴散態勢。其軌跡與中國對外投資、貿易往來的地理路徑高度重合,呈現出顯著的經濟地理特征。
教育階段下沉化。早期海外中文教育多集中在大學階段,如今快速向基礎教育階段下沉。這意味著學習者開始接觸中文的年齡更小,學習周期更長,效果也更穩固。
標準體系國際化。目前,中文水平考試(HSK)已在全球160多個國家設有1400多個考點,中文教育的評價標準在全球范圍內趨于一致,便利了人才流動與認證。

中新社記者:為什么越來越多國家將中文納入國民教育體系?這傳遞出什么信號?
王祎:將中文納入國民教育體系,是各國基于現實利益與長遠戰略的理性選擇。首先,從貿易依存度上看,中文已成為國際貿易語言和增收工具,直接驅動各國重視中文教育。
其次是人力資本溢價的顯現。在全球產業鏈中,特別是在國際物流、新能源、電子商務、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熟練掌握中文的本地雇員有不同程度的薪資溢價。這意味著投資中文教育就是投資本國人力資源的競爭力。
再次,數字基礎設施外溢效應帶動中文教育普及。在基礎設施建設、5G技術和人工智能等領域與中國合作緊密的國家將中文引入教育體系的意愿和速度明顯更高,說明技術標準的協同拉動了語言文化的學習需求。
這傳遞出一個清晰的信號:在全球公共產品的供給結構中,語言作為一種制度性權力和人力資本要素,其格局正在重塑。各國將中文納入國民教育體系,本質上是主動適應這一變革,為國家發展進行戰略性人力資本儲備。
中新社記者:有些國家將中文列入中學畢業考試或大學入學考試,這意味著什么?
王祎:這是更具標志性意義的舉措。目前,包括俄羅斯、愛爾蘭、白俄羅斯、匈牙利、英國、法國、南非等國家,相繼將中文列為中學畢業考試或大學入學考試的選考科目。
其深層含義不僅在于國家間的制度性互信,還體現各國精英篩選機制的重構與知識權力的遷移。通過考試這個指揮棒,中文在這些國家的社會認知中從一種工具性語言轉變為制度性語言,其影響力從市場層面上升到國家頂層設計。
中新社記者:各國對中文教育的重視為海外中文教育帶來怎樣的機遇與挑戰?
王祎:結構性的機遇與挑戰并存。機遇方面,國民教育體系的導入為海外中文教育市場帶來龐大、穩定的新增學習者群體,這為教材出版、數字教育平臺、師資培訓等整個產業鏈帶來空前發展機遇,也為中華文化國際傳播開拓更廣闊空間。同時,過去零散的、社團化的華文教育正在向標準化、規模化的教育產業轉化,催生了課程設計、教學評估、教育科技等專業化細分領域,海外中文教育迎來產業升級窗口期。
新挑戰同樣嚴峻。首先,“文化貼現”風險仍存。部分國家存在將中文教學窄化為商務漢語的傾向,過分強調其工具性,忽略語言所承載的文化與思想深度,可能使海外中文教育走向功利化和淺層化。其次,中國的教學標準與方法可能與海外的教育理念和文化習慣產生沖突,或導致標準適配的矛盾。如一些歐洲國家的教育體系更強調批判性思維和個性化表達,對標準化考試模式存在一定不適應。

中新社記者:當前在海外開展中文教育還存在哪些困難?從業者應當注意什么?
王祎:當前困難主要集中在兩大結構性障礙上。一是師資悖論。合格中文教師的全球需求缺口巨大,然而很多國家出于保護本國就業市場等多種原因,并未完全開放對中國籍教師的聘用,導致“有需求無崗位”的悖論。二是個別不友好聲音的干擾。在一些國家,中文教育被個別政客或媒體標簽化、政治化,以所謂“學術安全”為由進行限制,為中文教育的正常開展設置了非教育層面的障礙。
對此,海外中文教育從業者需堅持本土化融合,推動“中文+”模式落地,將中文與當地急需的職業技能結合。如在農業國家開發“中文+農業技術”課程,在旅游國家開發“中文+酒店管理”課程,讓中文真正扎根于當地社會經濟發展的土壤。此外,還需構建第三方認證,積極與國際通用教育體系接軌,通過國際通行認證提升中文教育的接受度與認可度,消減誤解中文教育的聲音。
總之,我們應更多將海外中文教育詮釋為提升個體競爭力、促進跨國合作的全球公共產品。促進語言學習回歸溝通與發展的本質,為構建更加互聯互通、相互理解的世界貢獻持久力量。(完)
受訪者簡介:

王祎,溫州大學華僑學院副院長、副研究員,俄羅斯人民友誼大學經濟學博士,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博士后,清華大學華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中國商業史學會華商研究專委會副主任。曾主持中國博士后基金、國務院僑辦、中國僑聯、浙江省社科聯等多項省部級課題和橫向課題。在《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華僑華人歷史研究》《世界僑情報告藍皮書》《當代國際移民政策國別研究》《八桂僑刊》等刊物發表多篇學術論文,撰寫資政報告30余篇。

東西問精選:
- 2025年11月15日 16:56:57
- 2025年11月14日 14:23:24
- 2025年11月13日 21:53:23
- 2025年11月13日 21:35:11
- 2025年11月12日 18:18:06
- 2025年11月12日 15:39:58
- 2025年11月11日 17:36:42
- 2025年11月10日 18:30:18
- 2025年11月09日 20:32:58
- 2025年11月09日 20:3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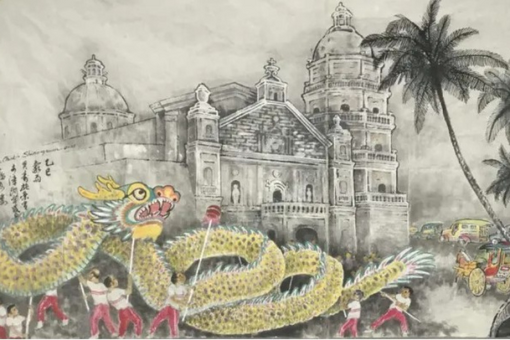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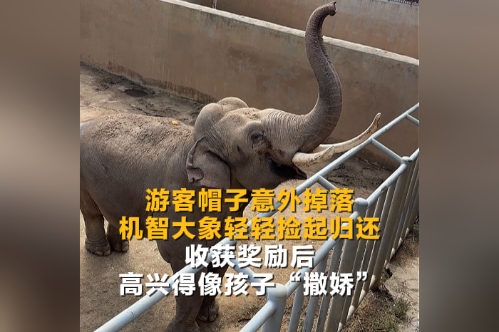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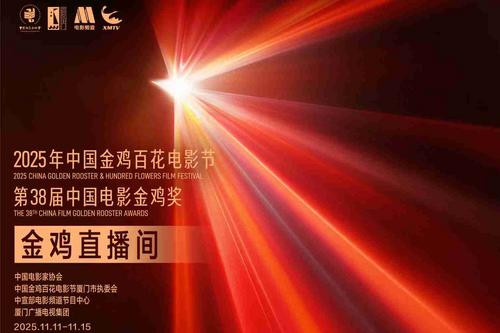










 京公網安備 11010202009201號
京公網安備 11010202009201號